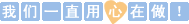日前的某天下午相继有俩美女来访。其一系友邦的资深营销员桃姐,过来为二炮和三丫的妈妈办理保险理赔手续;其二乃家在大朗的东莞土著九零后美眉阿菲,原在交警部门工作,双亲于莞邑一妙绝处辟有绿意葱茏的农场,说是春季甫过,荔枝开花,其父叶先生嘱其驾驶奥迪Q7送些新鲜荔枝蜂蜜过来给我们品尝润喉。对了,有人认为保险没用,甚至是骗人的,我却不这么看。尤其像友邦这种跨国集团公司,能够在世间屹立百年,抵御百年的风雨,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绝对不会骗人。 一通忙碌,吃过晚饭,正欲盥洗就寝,我的手机响了:十分罕见地有一长途电话呼入,拾起手机一看,却原来是远在海南的原洪江一中高一49班同学张志方,我高二53班班主任张书绅老师的大公子。我之前已听说,他毕业后一度尝试过多种不同的活法,也经历了一些不小的挫折,十数年前娶了个八零后的福建女孩做老婆,遂由深圳、珠海辗转去到琼岛发展。张志方告诉我,日内偶然看到有湖南老乡分享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的拙文《梦悠北窗自从容》,感慨良多,故此来电一叙别情。谁知他这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完全突破了我平素设置的社交通讯极限! “平生悔读五车书,历劫难迁尚姓愚。早悟文章鲜有准,浑忘权势灼于炉”! 直到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张志方高中毕业后复读了两届,1982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其时我已上大二,这么一论,彼此在岳麓山下还一块“混”了三年,作为一个地方出去的人,又有诸多渊源,他和我当时联系似乎还颇密切呢! “对景增慷慨,怆然念昔游”。而我手头正好有一本恩师、原湖南师大中文系主任马积高教授的线装诗集《风雨楼晚年诗钞》。诗中所写,不正是我今日之心情么?
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为国立师范学院,那是我生命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多少年来,子夜梦回,弦歌幽响,只能回味,却又不敢轻易涉足:远之长相思,近之情更怯。不是漠然,而是敬畏。 套用马翁的两句诗:“书生多意气,当年苦未酬”!在我们人生失意的时候,在我们一筹莫展、眼看行将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伟岸厚重仁慈的母校给了我们力量和信心。听说湖南师范大学眼下在全国有近四十万校友呢,我们做人的底气,来自岳麓山上沉默如血的巍巍红枫,来自日夜奔涌的滔滔湘江水。仁者高标浑似山,雅人深致清如水。梅能傲雪香能永,枫不经霜叶不红! 在对母校的怅然回望中,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赫石坡旁的岳王亭。1981年9月,中文系的新生全部安排在十舍,而十舍便矗立于赫石坡的东侧,湖边的岳王亭推窗可望。一池碧水,树影婆娑,当年人们总会看到一位沉默寡言的清瘦少年独自站立亭中,迎风垂目、横笛吹曲,一泻心中的愁闷,连同自己对未来的展望和期许。那个吹笛少年便是我。吹笛可以调理气息,养吾浩然之气。有时,我也会与好友张文勇斜挎小提琴拾级而上,来到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墓碑前肃穆凭吊,任飘飞的思绪兀自追赶远去的大雁…… “依然苦雨复愁风,又向汩罗访旧踪。欲上高亭觇远景,可怜平野入鸿濛”! 不说人尽皆知的云麓宫、爱晚亭,更别说麓山书院了。那些地名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于我而言,最是难忘,恐怕还有青枫峡,还有樟园。青枫峡是我大学四年经常读书散步的地方。在那儿,我曾经多次偶遇一位带着一条小黄狗嬉戏悠游的面目姣好的清纯少女。神奇的是,她那俊俏妩媚、带点淘气和娇嗔的模样,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来。那时一丁脸皮薄,还未学会与年轻的异性搭讪。不知她是本校低年级的学妹,抑或本校的教师子弟?从她的衣着与所牵的小黄狗来推测,她似乎更类后者。正常的在校生是不可能饲养宠物带在身边的。当时我想,她应该比我小三四岁,大约就是十五六岁的光景吧!模样真的特别乖巧,特别可爱。 樟园其实是语数楼前的一大片绿地。中文系、数学系的师生全部在这栋楼里办公、学习。是故樟园为我们上课、下课必经之所。记忆中当年的樟树甫及人高,长得茁壮的也至多不过两米左右的样子。如此看来,那片樟树应系七七、七八级师兄师姐们手植哟。说是樟园,实则午休时间或夜幕降临,这儿即幻变为高年级男女学生“谈露”的地方。何谓“谈露”?或乃“谈路”之误。长沙土话也!实即拍拖、谈恋爱,懂了吧?由于这儿总是三三两两、成双成对、卿卿我我,衣香鬓影,自觉的我们,平素反倒不怎么去樟园了。以免让人有偷窥之讥。心中却是无比向往的。自然,也有那顽皮和喜欢恶作剧的同学,故意专程绕路从樟园经过,侦查“敌情”、棒打鸳鸯。不是普通意义的“棒”,乃灼人的目光也! 其时有一耐人寻味的情况:外语系美女多,其他系的男生晚自习都争先恐后跑到外语系的教学楼里去占座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乜斜美女也! 而中文系才子多,其他系有那少数颇具机心冰雪聪明的美眉则多半会于晚自习的时候约上闺蜜跑来咱们中文系蹭“热度”、觅良人。 学校图书馆更不消说,那儿是全校正版书虫公认的大本营,且拥有全校除院办外唯一一台复印机。晚自习和周末跑去图书馆抢座位趁机觊觎美女帅哥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最是难忘,每天晚饭后我们总习惯三五成群或稀稀拉拉往湘江边溜达。名曰散步,实则海侃神吹,互通情报,顺便锻练身体。向彪、曹华、张小汉,夏子科、戈云琴、熊成刚、王志、陈立荣、姚新良、马宏铁,这些可都是当年与我一块散步的常伴哟,大多同年级不同系。自然,还有高年级的怀化老乡,毕业后留校,成为知名书法家和笛箫达人的胡昌华师兄,朝暾文学社(一丁忝任副社长)的骨干分子戈扬、蒋剑平、田飞君(现在叫田地)、周碧华、龚鹏飞,以及校乐队(一丁忝任乐队副队长、民乐组组长)拉小提琴的罗任重师兄、拉二胡的彭祝斌师弟、弹琵琶的黄瑜师妹,影视欣赏协会(一丁忝任理事长)的朱荣华、萧隆国、何彩章,和我一起同台演话剧的同年级同学叶坤妮、任莉,一起表演节目的施萍、熊丽莺、黄燕,包括后来成为湖湘名嘴、备受长沙各大学女生关注追捧继而不幸坠楼身亡的中文系83级师弟李尚能……等等。嗟夫,我复想起中文系老主任的诗句:“避疾难同人共醉,深居唯有鸟相知。无心风月随缘受,着手云烟故自奇”。
漫步湘江边可远眺桔子洲,有时还会见到星星点点的渔火,那多半是划着小船的渔民们正在湘江之上撒网打鱼。“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每天散步的时间可长可短,全由自己把握。最少一小时,时间长兴致好的时候便总得两三个小时呢,甚至拖到宿舍熄灯才轻手轻脚摸回寝室。途中若是遇雨,便个个都成落汤鸡了! 最是难忘,77级毕业离校前夕在三舍灯光球场的那台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激情的晚会。
三舍乃学生们庆贺女排三连冠砸盆摔碗扔热水瓶的“重灾区”,电影《少林寺》走红的时候又成为年轻气盛的男生们研习拳脚功夫的地方。学校的文艺演出,人少的时候一般放在院办公楼的大礼堂,人多的时候则一概安排在三舍灯光球场。我的大学毕业留言本上有一则留言十分精彩: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我看见风度翩翩的玛斯加里尔侯爵拄着雨伞、穿着雨靴从舞台上蹒跚走过…… ——说的便是我出演莫里哀喜剧《可笑的女才子》男1号玛斯戛里尔侯爵的幽默往事。当年条件有限、道具欠奉,临阵磨枪,只好以雨伞雨靴代替真皮马靴和英国绅士专用的洋气遮阳伞。 却说中文系77级师兄孙健林那晚表演的乃饱含深情,长达半小时的配乐诗朗诵:《毕业之歌》。台下黑压压一片,最少坐了几千人。孙师兄朗诵至动情处,台下一片抽泣之声!“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节目表演完毕后那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至今犹然回响在我耳畔。孙师兄毕业后留校做了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助教,天生别材,多年后弃教从政,2000年左右改任湘西自治州州委组织部部长;2006年有一次寻访故人,我在吉首民族宾馆见到了他,二人聊了很久;同时还结识了时任该市市长的鲍忠银先生。
尹长民、李秋枫、林增平、张楚廷、戴海、周寅宾、周秉钧、马积高、吴容甫、杨安仑、汪名凡、彭恺奇、舒其蕙、鲍厚星、张会恩、陶先淮、凌宇、陈汉章……这些老校长、老教授、老教师:在我记忆的天空里,他们的名字像流星一样划过,灼灼其华、星光灿烂!数十年来,复如骊歌,若陈酿,似酽茶,一直温暖着我异乡的寂寥梦境,加持着我奋斗抗争人生的神奇法力。
2020年5月17日凌晨草成于中国作家第一村·点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