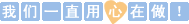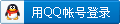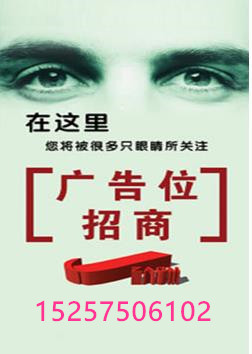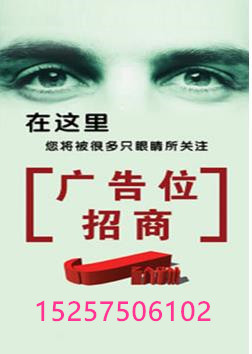田迎人黑白油画《胡同深处的白塔》
2018-11-15 16:33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阅读:702次 我要评论
田迎人黑白油画《胡同深处的白塔》
作者 彭 俐
古都北京有两座很有名的白塔,在一片灰色四合院建筑中格外醒目,一座是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另一座是阜城门内妙应寺里的白塔。

这一对美丽的浮屠,装点着历史悠久的城郭,白昼犹如“并蒂莲”婀娜绽放,夜晚仿佛“双子星”通透晶莹。二者虽然同为藏式喇嘛塔,但其身份认定却大异其趣。北海白塔的身世显赫,矗立皇家园林之中,骄傲的公主一般,昂首天外,睥睨苍茫;妙应寺白塔则屈尊降贵,携手胡同低矮、简朴民舍,甘与城市平民为伍,怀抱着隐居林泉的高士情操。
然而,姊妹二塔结伴,京城灵庙不孤。
不似西安大雁塔“一只”,开封铁塔“一杵”,苏州虎丘塔“一岗”,杭州雷峰塔(黄妃塔)“一妃”……
画家田迎人,性格本就孤高,一生不做锦上添花之事,百年愿为雪中送炭之人。于是,她最先选择了名气与身价似乎都不如北海白塔的“灰姑娘”——妙应寺白塔,做她画室中朝夕相伴的尊贵模特。
一睹田画家的这幅黑白油画——《胡同深处的白塔》,眼泪差点儿掉下来。虽然居者不见容貌,而窘况颇可唏嘘,房屋简陋到搭建,电线凌乱在空中,屋檐低小到埋首,瓦片侵蚀到变形……而那尊白塔依旧洁白,依旧拔俗,甚至依旧典雅、高贵,仿佛信念依旧高耸!
此时的白塔愈显其突兀、高大,也愈显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建立在现实社会与人生的坚实基础之上,不再是轻飘之辈的轻浮之笔所描摹,也不是那些涂脂抹粉之能事可同日而语。画作如人,怜恤苍生。这源于多么美丽动人的善念,出自多么真挚、素朴的善根。而整个画面所营造的稳健与安宁,让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奢望与躁动的情绪存在。这让我们想起孔老夫子的喟叹:“一箪食、一漂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是一种自古以来仁人君子的处世之风范,也是画家诗人处理社会生活题材时的一种情怀和境界。
自从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以来,两千多年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华大地上寺庙与佛陀渐渐增多,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袈裟随处可见,梵唱几度悠扬,正如诗人杜牧所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类似关于寺庙与佛事的诗词歌赋很多,大多是秀丽江南的人伦风物所系,再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籍《枫桥夜泊》)”;“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白居易《题大林寺桃花》)”;“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等,却显见北方大地的文人题咏,而四大佛教名山四分之三属南国(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唯有山西五台山屹立北土。于是,古典名诗名画得江山之助者尽在江南。想当年,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在皇家画院出考题——《深山藏古寺》,曾难倒画师无数,却难不住今天的画家田迎人。她的“深山古寺”之“深山”,是古都之“闹市”,古人不曰:“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我们所见田画家笔下的“白衣卿相”——即妙应寺(始建于1271年,高50.9米)白塔,他隐居在都城偏西之闹市的胡同里,隐身在平头百姓的住所之间,隐忍而又倔强的峭立人间700多年,比那身为“皇亲国戚”的北海白塔(始建于1651年,高35.9米)身量更高,比故宫(始建于1406年)更加古老,比天坛(始建于1420年)还要资深,它总是以清清爽爽的面目示人,以白璧无瑕的心意立身,以高标出尘的磊落处世……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热门图片
Copyright © 绍兴微平台 All rights reserved 浙ICP备13027338号-1
版权所有:绍兴头条网 热线:0575-88051334 15257506102 绍兴头条网:QQ2805735231@qq.com,1303647702@qq.com 联系地址:绍兴市东昇苑南区四幢504室免责声明:本站系自媒体平台,只提供交流信息,所有文章、贴子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害到您的合法权益,请您积极向我们投诉。我们将作删稿处理!
Powered by ZmSys.com 本站禁止色情、政治、反动等国家法律不允许的内容,注意自我保护,谨防上当受骗